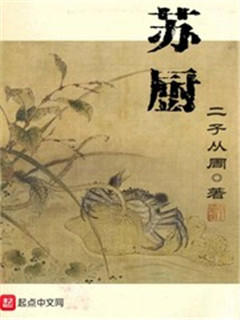- [ 免费 ] 第一章 眉山
- [ 免费 ] 第二章 嘴炮堂哥
- [ 免费 ] 第三章 程家
- [ 免费 ] 第四章 苏八娘
- [ 免费 ] 第五章 血旺
- [ 免费 ] 第六章 鸡茸和开水白菜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章 病根
- [ 免费 ] 第八章 肚里有料
- [ 免费 ] 第九章 风投
- [ 免费 ] 第十章 讲究人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物价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牛杂可是好东西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精盐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好菜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名声也是个好东西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仓舒转世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斗茶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小康标准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苏家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 明道致用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 求字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二章 试烧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三章 瓷片
- [ 免费 ] 第二十四章 史洞修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五章 纸
- [ 免费 ] 第二十六章 新酒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七章 定价
- [ 免费 ] 第二十八章 玉瓷
- [ 免费 ] 第二十九章 理科
- [ 免费 ] 第三十章 县令
- [ 免费 ] 第三十一章 徒弟
- [ 免费 ] 第三十二章 石通
- [ 免费 ] 第三十三章 账本
- [ 免费 ] 第三十四章 蚀刻
- [ 免费 ] 第三十五章 产业布局
- [ 免费 ] 第三十六章 仲先公
- [ 免费 ] 第三十七章 羽毛纹的花钢 ...
- [ 免费 ] 第三十八章 侧跳
- [ 免费 ] 第三十九章 弃儿
- [ 免费 ] 第四十章 生计
- [ 免费 ] 第四十一章 铁锅
- [ 免费 ] 第四十二章 八菜一汤
- [ 免费 ] 第四十三章 张象中
- [ 免费 ] 第四十四章 元素周期
- [ 免费 ] 第四十五章 张天师
- [ 免费 ] 第四十六章 石家
- [ 免费 ] 第四十七章 基建
- [ 免费 ] 第四十八章 上表
- [ 免费 ] 第四十九章 蜂窝煤
- [ 免费 ] 第五十章 沙金
- [ 免费 ] 第五十一章 加油
- [ 免费 ] 第五十二章 卖鱼搭档
- [ 免费 ] 第五十三章 讹诈
- [ 免费 ] 第五十四章 学习
- [ 免费 ] 第五十五章 老军
- [ 免费 ] 第五十六章 十字歌
- [ 免费 ] 第五十七章 瓷码
- [ 免费 ] 第五十八章 方法论
- [ 免费 ] 第五十九章 河帮雏形
- [ 免费 ] 第六十章 仿宋体
- [ 免费 ] 第六十一章 曲榷协议
- [ 免费 ] 第六十二章 豆花饭
- [ 免费 ] 第六十三章 扎染
- [ 免费 ] 第六十四章 早饭
- [ 免费 ] 第六十五章 理工
- [ 免费 ] 第六十六章 取酒
- [ 免费 ] 第六十七章 制曲
- [ 免费 ] 第六十八章 大苏小苏
- [ 免费 ] 第六十九章 雀谱
- [ 免费 ] 第七十章 授课
- [ 免费 ] 第七十一章 文理
- [ 免费 ] 第七十二章 轴承与来信 ...
- [ 免费 ] 第七十三章 看破说破
- [ 免费 ] 第七十四章 混乱
- [ 免费 ] 第七十五章 工具
- [ 免费 ] 第七十六章 在藜将军
- [ 免费 ] 第七十七章 蛮部
- [ 免费 ] 第七十八章 指点
- [ 免费 ] 第七十九章 竹屋
- [ 免费 ] 第八十章 观瓷
- [ 免费 ] 第八十一章 珠串
- [ 免费 ] 第八十二章 常数
- [ 免费 ] 第八十三章 开城
- [ 免费 ] 第八十四章 能人
- [ 免费 ] 第八十五章 返乡
- [ 免费 ] 第八十六章 松花蛋
- [ 免费 ] 第八十七章 私奔
- [ 免费 ] 第八十八章 娃娃亲
- [ 免费 ] 第八十九章 茭白
- [ 免费 ] 第九十章 孝心
- [ 免费 ] 第九十一章 浮圆
- [ 免费 ] 第九十二章 模棱公
- [ 免费 ] 第九十三章 宴席初步
- [ 免费 ] 第九十四章 去势
- [ 免费 ] 第九十五章 蛋
- [ 免费 ] 第九十六章 冲压
- [ 免费 ] 第九十七章 划时代
- [ 免费 ] 第九十八章 千分尺
- [ 免费 ] 第九十九章 温度计
- [ 免费 ] 第一百章 等距螺旋
- [ 免费 ] 第一百零一章 鸭雏
- [ 免费 ] 第一百零二章 告状
- [ 免费 ] 第一百零三章 鳝鱼
- [ 免费 ] 第一百零四章 买山
- [ 免费 ] 第一百零五章 龙脑
- [ 免费 ] 第一百零六章 五金博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零七章 扇翅膀
- [ 免费 ] 第一百零八章 无聊
- [ 免费 ] 第一百零九章 几本书不如二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一十章 对对子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一十一章 埋祟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一十二章 卖痴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一十三章 女婿上门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一十四章 商议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一十五章 相处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一十六章 告祖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一十七章 堂哥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一十八章 送穷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一十九章 大宋自己的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二十章 代差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二十一章 蚕市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二十二章 精品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二十三章 薛忠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二十四章 别人的奇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二十五章 被打脸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二十六章 翊卫仙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二十七章 胜利的大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二十八章 灵光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二十九章 李老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三十章 惨相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三十一章 重逢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三十二章 苛政酷毒,犹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三十三章 铜镜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三十四章 绿茶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三十五章 来访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三十六章 考较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三十七章 风筝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三十八章 大洪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三十九章 展布
- [ 免费 ] 第一百四十章 危机与对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四十一章 面涅将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四十二章 平南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四十三章 小书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四十四章 不要脸的老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四十五章 随手功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四十六章 君君臣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四十七章 共读
- [ 免费 ] 第一百四十八章 李运
- [ 免费 ] 第一百四十九章 龙老头的幸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五十章 变化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五十一章 程夫人的担心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五十二章 玩香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五十三章 马屁炸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五十四章 陈慥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五十五章 伟大的航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五十六章 小东西大工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五十七章 斗智不斗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五十八章 东川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五十九章 玄香太守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六十章 大理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六十一章 高兄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六十二章 马本纲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六十三章 对策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六十四章 踪迹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六十五章 第一个承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六十六章 童谣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六十七章 纵横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六十八章 反扑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六十九章 神话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七十章 快递小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七十一章 陆路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七十二章 阿囤赤尊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七十三章 阿囤元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七十四章 范先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七十五章 宝贵的炉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七十六章 陈希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七十七章 长刀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七十八章 大巫
- [ 免费 ] 第一百七十九章 雄辩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八十章 洗脑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八十一章 尊重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八十二章 小心的祭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八十三章 恐怖的神灵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八十四章 布置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八十五章 天威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八十六章 酥油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八十七章 代价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八十八章 挨揍
- [ 免费 ] 第一百八十九章 养屁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九十章 戒尺要开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九十一章 还是挨打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九十二章 短板
- [ 免费 ] 第一百九十三章 鸡丁
- [ 免费 ] 第一百九十四章 第一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九十五章 小报
- [ 免费 ] 第一百九十六章 虚惊
- [ 免费 ] 第一百九十七章 倒春寒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九十八章 套小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百九十九章 定期活期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章 贺礼
- [ 免费 ] 第二百零一章 可龙里号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零二章 烧白
- [ 免费 ] 第二百零三章 水泥
- [ 免费 ] 第二百零四章 求情
- [ 免费 ] 第二百零五章 有所求
- [ 免费 ] 第二百零六章 箭课
- [ 免费 ] 第二百零七章 破甲锥
- [ 免费 ] 第二百零八章 心累
- [ 免费 ] 第二百零九章 北极院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一十章 眼镜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一十一章 托请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一十二章 同学纪念册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一十三章 新船设计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一十四章 成都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一十五章 铂金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一十六章 例题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一十七章 桥的题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一十八章 张天选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一十九章 俩花熊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二十章 买房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二十一章 打望,不可能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二十二章 大游江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二十三章 花边故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二十四章 诗会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二十五章 美质良才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二十六章 一地鸡毛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二十七章 小张方平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二十八章 对与错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二十九章 论计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三十章 冠礼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三十一章 孩子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三十二章 苏伯纯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三十三章 为中华之崛起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三十四章 赵忭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三十五章 打探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三十六章 《尚书》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三十七章 《尚书祈询》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三十八章 十二平均律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三十九章 白龟的名字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四十章 鳜鱼肥
- [ 免费 ] 第二百四十一章 不作为和瞎作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四十二章 永康军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四十三章 出事
- [ 免费 ] 第二百四十四章 鹤胫弩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四十五章 乞第龙山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四十六章 惩罚和教育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四十七章 时疫
- [ 免费 ] 第二百四十八章 至宝丹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四十九章 措施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五十章 弹劾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五十一章 病愈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五十二章 拴住结婚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五十三章 控鹤军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五十四章 少年行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五十五章 织锦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五十六章 出发准备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五十七章 南行集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五十八章 天下最穷处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五十九章 学区房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六十章 王安石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六十一章 欧阳修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六十二章 《上欧阳内翰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六十三章 老太君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六十四章 两道菜做六天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六十五章 请解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六十六章 汴京风华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六十七章 大相国寺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六十八章 万姓大集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六十九章 勋戚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七十章 王韶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七十一章 船到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七十二章 新楼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七十三章 汴京腊月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七十四章 磨刀石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七十五章 内官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七十六章 梅尧臣去世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七十七章 解试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七十八章 大比
- [ 免费 ] 第二百七十九章 殿试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八十章 写文章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八十一章 强作解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八十二章 看榜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八十三章 谢恩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八十四章 琼林宴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八十五章 授官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八十六章 为国考试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八十七章 判卷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八十八章 报道
- [ 免费 ] 第二百八十九章 救日
- [ 免费 ] 第二百九十章 建言
- [ 免费 ] 第二百九十一章 改造
- [ 免费 ] 第二百九十二章 马上草赋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九十三章 辽人临观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九十四章 夜校
- [ 免费 ] 第二百九十五章 国舅
- [ 免费 ] 第二百九十六章 游园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九十七章 致用之学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九十八章 徘徊太多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百九十九章 衣锦还乡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章 再见张方平
- [ 免费 ] 第三百零一章 夔州
- [ 免费 ] 第三百零二章 烟笋排骨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零三章 帮手
- [ 免费 ] 第三百零四章 翻译官
- [ 免费 ] 第三百零五章 熟蛮
- [ 免费 ] 第三百零六章 转运判官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零七章 水转大纺车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零八章 炽火的开解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零九章 计谋被识破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一十章 战斗打响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一十一章 输了!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一十二章 封路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一十三章 爱听评书的战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一十四章 嘉奖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一十五章 小油会做官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一十六章 灵柴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一十七章 狐大仙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一十八章 狐大仙搬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一十九章 九斗碗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二十章 驾崩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二十一章 闹剧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二十二章 老堂哥开炮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二十三章 劝解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二十四章 朝廷大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二十五章 夔州奏报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二十六章 布置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二十七章 逃跑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二十八章 重见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二十九章 铁门关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三十章 王文郁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三十一章 密谋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三十二章 高宾图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三十三章 苏颂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三十四章 图经本草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三十五章 制度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三十六章 朝会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三十七章 家家一地鸡毛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三十八章 冲突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三十九章 夏使
- [ 免费 ] 第三百四十章 奏对
- [ 免费 ] 第三百四十一章 刺勇之议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四十二章 争论
- [ 免费 ] 第三百四十三章 建议
- [ 免费 ] 第三百四十四章 各怀心思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四十五章 分析
- [ 免费 ] 第三百四十六章 局面
- [ 免费 ] 第三百四十七章 潜移默化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四十八章 军靴
- [ 免费 ] 第三百四十九章 实心任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五十章 再见苏轼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五十一章 渭州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五十二章 变态繁荣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五十三章 蔡确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五十四章 断案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五十五章 镇戎军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五十六章 苏容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五十七章 向守忠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五十八章 富弼的炮轰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五十九章 小隐君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六十章 纲领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六十一章 李老员外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六十二章 没有酱油的羊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六十三章 掌心雷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六十四章 天下兴亡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六十五章 马鹿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六十六章 火边子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六十七章 问题的本质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六十八章 说情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六十九章 被抛弃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七十章 演习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七十一章 理论核心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七十二章 财计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七十三章 火炮初议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七十四章 河湟变迁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七十五章 董毡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七十六章 治平骑刀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七十七章 诚意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七十八章 理学讨论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七十九章 交相辉映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八十章 学问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八十一章 天都山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八十二章 司竹监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八十三章 震天雷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八十四章 羊毛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八十五章 李文钊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八十六章 嵬名浪遇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八十七章 叛逃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八十八章 对答
- [ 免费 ] 第三百八十九章 秋娘
- [ 免费 ] 第三百九十章 被吓和吓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九十一章 梁屹多埋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九十二章 谈判
- [ 免费 ] 第三百九十三章 橄榄球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九十四章 变化中的渭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九十五章 天时
- [ 免费 ] 第三百九十六章 计较
- [ 免费 ] 第三百九十七章 运动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九十八章 王文郁的心思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百九十九章 抬杠之旅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章 物尽其用
- [ 免费 ] 第四百零一章 好年景
- [ 免费 ] 第四百零二章 李文钊的背景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零三章 朝堂的分析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零四章 家粱的判断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零五章 环庆
- [ 免费 ] 第四百零六章 外快
- [ 免费 ] 第四百零七章 三打九
- [ 免费 ] 第四百零八章 折锐
- [ 免费 ] 第四百零九章 尖厉獠牙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一十章 弹劾来了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一十一章 最大赢家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一十二章 老张与王二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一十三章 劝降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一十四章 接战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一十五章 战壕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一十六章 神迹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一十七章 表面上的不利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一十八章 义勇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一十九章 水火交逼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二十章 冲击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二十一章 威猛的石薇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二十二章 大捷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二十三章 战后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二十四章 平话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二十五章 红旗犹带冷梅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二十六章 姐妹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二十七章 前朝旧事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二十八章 他怎么敢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二十九章 计相学宫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三十章 再次通报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三十一章 大阅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三十二章 西方的文明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三十三章 一类人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三十四章 请假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三十五章 两宫之意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三十六章 必须姓苏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三十七章 很尴尬吧?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三十八章 日历计算器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三十九章 还乡
- [ 免费 ] 第四百四十章 再见可龙里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四十一章 众人
- [ 免费 ] 第四百四十二章 婚前
- [ 免费 ] 第四百四十三章 迎娶
- [ 免费 ] 第四百四十四章 洞房
- [ 免费 ] 第四百四十五章 婚后
- [ 免费 ] 第四百四十六章 再次出发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四十七章 巡视
- [ 免费 ] 第四百四十八章 试射
- [ 免费 ] 第四百四十九章 一路上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五十章 再到东川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五十一章 国王跑了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五十二章 退军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五十三章 铜矿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五十四章 渡口镇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五十五章 乐于县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五十六章 高塔大殿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五十七章 嶲州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五十八章 濮议
- [ 免费 ] 第四百五十九章 苏洵去世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六十章 第三个自己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六十一章 换俘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六十二章 赵曙生病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六十三章 墓志铭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六十四章 财政赤字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六十五章 新君举措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六十六章 欧阳修出事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六十七章 彻底失控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六十八章 意大利炮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六十九章 神机铳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七十章 生意和神器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七十一章 议论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七十二章 进京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七十三章 生活与生存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七十四章 论政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七十五章 谁改变谁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七十六章 谁也改变不了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七十七章 小妹的男朋友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七十八章 天文讨论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七十九章 劝谏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八十章 货物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八十一章 种谔的攻略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八十二章 复绥州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八十三章 越次入对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八十四章 谅祚之死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八十五章 诛叛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八十六章 铁腕计相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八十七章 鳌山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八十八章 元宵节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八十九章 游玩
- [ 免费 ] 第四百九十章 经济影响力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九十一章 皇宋银行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九十二章 红脸白脸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九十三章 纲要
- [ 免费 ] 第四百九十四章 金奖
- [ 免费 ] 第四百九十五章 挂绫查账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九十六章 密会
- [ 免费 ] 第四百九十七章 水傀儡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百九十八章 讨论
- [ 免费 ] 第四百九十九章 开幕式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章 女骑
- [ 免费 ] 第五百零一章 没有盐
- [ 免费 ] 第五百零二章 解决
- [ 免费 ] 第五百零三章 第一笔收入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零四章 何为先
- [ 免费 ] 第五百零五章 择术为先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零六章 阿云案
- [ 免费 ] 第五百零七章 法律精神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零八章 新宫殿
- [ 免费 ] 第五百零九章 道德标杆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一十章 万货集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一十一章 皇宋宝钞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一十二章 地震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一十三章 应变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一十四章 护送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一十五章 夫妻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一十六章 分析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一十七章 天方夜谭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一十八章 孙能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一十九章 河害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二十章 议河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二十一章 董员外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二十二章 横有横的资本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二十三章 河鲜宴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二十四章 孙能的进步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二十五章 大名府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二十六章 察人之术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二十七章 赵郡李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二十八章 安抚使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二十九章 都是熟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三十章 单舟对敌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三十一章 打嘴仗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三十二章 连消带打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三十三章 看图说话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三十四章 刮目相看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三十五章 皇后管内库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三十六章 平戎策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三十七章 唐介病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三十八章 王安石的课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三十九章 天变人事的另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四十章 国有军工企业的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四十一章 军器监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四十二章 嵩阳书院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四十三章 古怪的正确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四十四章 均输法的弊端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四十五章 军工和三产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四十六章 十大罪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四十七章 风波
- [ 免费 ] 第五百四十八章 叔叔驳侄儿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四十九章 再见章惇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五十章 论《青苗法》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五十一章 讨论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五十二章 分析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五十三章 讲解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五十四章 贷与赈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五十五章 战术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五十六章 荆湖建议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五十七章 水利农田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五十八章 三产
- [ 免费 ] 第五百五十九章 三不足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六十章 进与退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六十一章 苏大嘴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六十二章 斗争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六十三章 郭淮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六十四章 骑兵铳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六十五章 父子佳话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六十六章 颁奖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六十七章 士子闹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六十八章 我军器监就需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六十九章 苏元贞的去向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七十章 苏轼被弹劾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七十一章 你们越线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七十二章 利益交换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七十三章 李定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七十四章 西夏人的进攻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七十五章 枢密院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七十六章 要求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七十七章 经略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七十八章 出发
- [ 免费 ] 第五百七十九章 隔断天都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八十章 萧关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八十一章 破关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八十二章 胜利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八十三章 士德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八十四章 游说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八十五章 保甲法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八十六章 新政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八十七章 梦想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八十八章 大饼
- [ 免费 ] 第五百八十九章 民夫
- [ 免费 ] 第五百九十章 西夏历史文明展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九十一章 倒逼
- [ 免费 ] 第五百九十二章 纵横
- [ 免费 ] 第五百九十三章 传说
- [ 免费 ] 第五百九十四章 温饱线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九十五章 改革和叛乱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九十六章 送行与教育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九十七章 广锐军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百九十八章 兵变
- [ 免费 ] 第五百九十九章 永兴军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章 吴逵
- [ 免费 ] 第六百零一章 求情
- [ 免费 ] 第六百零二章 自劾
- [ 免费 ] 第六百零三章 宾化
- [ 免费 ] 第六百零四章 刘嗣当官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零五章 陪伴
- [ 免费 ] 第六百零六章 模范村
- [ 免费 ] 第六百零七章 芭夯兔
- [ 免费 ] 第六百零八章 交流轮训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零九章 冲击相府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一十章 事件始末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一十一章 富弼返洛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一十二章 梳理军政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一十三章 扁罐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一十四章 检查组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一十五章 提前布局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一十六章 都难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一十七章 湘乡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一十八章 大打出手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一十九章 打仗打出来的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二十章 利弊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二十一章 弊端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二十二章 公事公办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二十三章 瑶族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二十四章 禅师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二十五章 苏方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二十六章 开梅山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二十七章 逼婚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二十八章 方田均税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二十九章 明光铠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三十章 上香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三十一章 解释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三十二章 疯狗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三十三章 佞人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三十四章 召回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三十五章 相迎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三十六章 课程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三十七章 思想体系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三十八章 去处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三十九章 街坊
- [ 免费 ] 第六百四十章 赐第
- [ 免费 ] 第六百四十一章 陛见
- [ 免费 ] 第六百四十二章 见解
- [ 免费 ] 第六百四十三章 老太君的智慧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四十四章 大宋东方朔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四十五章 《金石图录》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四十六章 大夏龙雀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四十七章 开封府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四十八章 宰相马,一样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四十九章 冷处理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五十章 调研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五十一章 罚铜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五十二章 蔡确的骚操作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五十三章 又见王雱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五十四章 调查报告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五十五章 反问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五十六章 建议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五十七章 木征的逆袭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五十八章 河州复失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五十九章 天文历法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六十章 天数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六十一章 苏油是好同志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六十二章 职田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六十三章 大妈护井团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六十四章 大工程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六十五章 上课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六十六章 治河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六十七章 卫朴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六十八章 失踪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六十九章 推演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七十章 分析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七十一章 烤串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七十二章 承包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七十三章 好消息不断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七十四章 《免行法》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七十五章 忠烈祠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七十六章 鸡西儿巷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七十七章 命案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七十八章 金姐儿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七十九章 蛛丝马迹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八十章 布置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八十一章 收网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八十二章 拜访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八十三章 家书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八十四章 大朝会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八十五章 麒麟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八十六章 分类学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八十七章 通天贴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八十八章 玉津园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八十九章 国家预算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九十章 王韶入京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九十一章 吐蕃智将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九十二章 覆军
- [ 免费 ] 第六百九十三章 君臣之争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九十四章 八公来了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九十五章 旱情苗头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百九十六章 运粮
- [ 免费 ] 第六百九十七章 小官
- [ 免费 ] 第六百九十八章 蔡京
- [ 免费 ] 第六百九十九章 姜是老的辣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章 乌龙
- [ 免费 ] 第七百零一章 蛮干
- [ 免费 ] 第七百零二章 大胜
- [ 免费 ] 第七百零三章 流民图
- [ 免费 ] 第七百零四章 求退
- [ 免费 ] 第七百零五章 小人之心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零六章 商议
- [ 免费 ] 第七百零七章 多少是一点点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零八章 老酒
- [ 免费 ] 第七百零九章 下雨了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一十章 为君之道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一十一章 离京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一十二章 诗人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一十三章 重会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一十四章 名妓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一十五章 太湖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一十六章 大工程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一十七章 旱情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一十八章 游说各方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一十九章 举措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二十章 奸臣分析奸臣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二十一章 利益交换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二十二章 到任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二十三章 盐户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二十四章 少年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二十五章 巨舰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二十六章 平家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二十七章 日本鬼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二十八章 字典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二十九章 祢衡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三十章 常州与饶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三十一章 手实法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三十二章 章惇的狙击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三十三章 贾宪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三十四章 顶级数学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三十五章 船坞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三十六章 视察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三十七章 两首词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三十八章 谁剽窃谁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三十九章 恶作剧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四十章 安和圩
- [ 免费 ] 第七百四十一章 砻磨
- [ 免费 ] 第七百四十二章 蟹粉
- [ 免费 ] 第七百四十三章 言传身教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四十四章 晒盐场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四十五章 突然有钱也不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四十六章 礼尚往来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四十七章 昌国县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四十八章 招募
- [ 免费 ] 第七百四十九章 三娘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五十章 海鲜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五十一章 蚝油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五十二章 潮报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五十三章 大盘子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五十四章 咖啡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五十五章 争议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五十六章 上报中央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五十七章 笔名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五十八章 两浙风味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五十九章 石薇的决定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六十章 各方反应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六十一章 聊上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六十二章 寻死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六十三章 花花绕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六十四章 驸马难当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六十五章 没活明白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六十六章 火灾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六十七章 章惇的算计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六十八章 错过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六十九章 晚了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七十章 旗帜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七十一章 船队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七十二章 再见章惇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七十三章 出发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七十四章 山寨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七十五章 溪口战役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七十六章 夜战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七十七章 秋风扫落叶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七十八章 见老乡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七十九章 大案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八十章 打鱼摸虾甲天下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八十一章 劝说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八十二章 漏勺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八十三章 紫砂壶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八十四章 模式的胜利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八十五章 黄鱼季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八十六章 沈括的外交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八十七章 文会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八十八章 王安石的局面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八十九章 李士宁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九十章 交通规划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九十一章 吕惠卿贬官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九十二章 枪榴弹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九十三章 劳动人民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九十四章 天变应在辽国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九十五章 辽国之变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九十六章 交趾入侵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九十七章 朝廷知闻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百九十八章 议事
- [ 免费 ] 第七百九十九章 枢密副使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章 内奸
- [ 免费 ] 第八百零一章 情报分析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零二章 出兵
- [ 免费 ] 第八百零三章 见面礼
- [ 免费 ] 第八百零四章 老朋友见面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零五章 誓师
- [ 免费 ] 第八百零六章 火箭
- [ 免费 ] 第八百零七章 廷议
- [ 免费 ] 第八百零八章 定议
- [ 免费 ] 第八百零九章 刺客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一十章 联军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一十一章 吕惠卿的鱼死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一十二章 没卵子的大象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一十三章 殉爆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一十四章 小胜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一十五章 重挫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一十六章 决战在即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一十七章 元江水师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一十八章 相互算计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一十九章 处处烽火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二十章 水战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二十一章 炮火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二十二章 炮击升龙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二十三章 来使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二十四章 条件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二十五章 黎太后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二十六章 决战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二十七章 杀戮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二十八章 齐射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二十九章 解决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三十章 沸腾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三十一章 拐点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三十二章 送行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三十三章 矛盾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三十四章 公平的方案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三十五章 杨曙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三十六章 章法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三十七章 理政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三十八章 会飞的货物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三十九章 宝马
- [ 免费 ] 第八百四十章 断刑
- [ 免费 ] 第八百四十一章 改革
- [ 免费 ] 第八百四十二章 王韶醒了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四十三章 十三郎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四十四章 李舜举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四十五章 南宋
- [ 免费 ] 第八百四十六章 大利
- [ 免费 ] 第八百四十七章 请求移民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四十八章 廖恩
- [ 免费 ] 第八百四十九章 真腊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五十章 大鱼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五十一章 支持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五十二章 捕象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五十三章 吴哥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五十四章 辽国中衰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五十五章 宗兄使辽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五十六章 建设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五十七章 回交州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五十八章 交趾新年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五十九章 张载逝世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六十章 微服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六十一章 参观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六十二章 扁罐的书房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六十三章 商品交易会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六十四章 蒲珊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六十五章 蒲珊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六十六章 商议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六十七章 龙牙港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六十八章 炮弹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六十九章 张道长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七十章 老张的有机化学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七十一章 平炉和高炉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七十二章 基地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七十三章 矿区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七十四章 蒲释马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七十五章 海战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七十六章 逃跑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七十七章 大火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七十八章 签字
- [ 免费 ] 第八百七十九章 锡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八十章 缺女人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八十一章 嫁妆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八十二章 论功过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八十三章 相州案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八十四章 议定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八十五章 聚会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八十六章 砗磲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八十七章 铁板钓鱼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八十八章 舆情
- [ 免费 ] 第八百八十九章 大法螺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九十章 海运
- [ 免费 ] 第八百九十一章 玩翡翠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九十二章 把控大市场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九十三章 螺旋桨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九十四章 大工程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九十五章 郑州对话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九十六章 结案
- [ 免费 ] 第八百九十七章 验尸
- [ 免费 ] 第八百九十八章 苏颂的态度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百九十九章 软糖
- [ 免费 ] 第九百章 缝纫机
- [ 免费 ] 第九百零一章 起义
- [ 免费 ] 第九百零二章 建设兵团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零三章 专业
- [ 免费 ] 第九百零四章 交趾急奏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零五章 人民战争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零六章 两分五
- [ 免费 ] 第九百零七章 各有勾当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零八章 陈田
- [ 免费 ] 第九百零九章 董大官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一十章 商议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一十一章 奇怪的战争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一十二章 哭廷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一十三章 新闻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一十四章 瓮城战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一十五章 曹南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一十六章 守会安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一十七章 大败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一十八章 追击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一十九章 诃黎之死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二十章 劝谏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二十一章 赵顼的家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二十二章 殿试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二十三章 程氏兄弟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二十四章 解封卷子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二十五章 唱名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二十六章 上香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二十七章 密计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二十八章 巡视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二十九章 横山关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三十章 世家的养成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三十一章 程岳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三十二章 旧州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三十三章 刘蛟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三十四章 邹时阑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三十五章 盛世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三十六章 远虑纤图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三十七章 值得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三十八章 薏仁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三十九章 唐慎微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四十章 再见吕惠卿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四十一章 西事
- [ 免费 ] 第九百四十二章 启程
- [ 免费 ] 第九百四十三章 秉常
- [ 免费 ] 第九百四十四章 李清
- [ 免费 ] 第九百四十五章 御史们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四十六章 诗案
- [ 免费 ] 第九百四十七章 王营
- [ 免费 ] 第九百四十八章 审理
- [ 免费 ] 第九百四十九章 招供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五十章 商量对策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五十一章 乌台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五十二章 对阵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五十三章 谢表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五十四章 突发事件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五十五章 枉作小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五十六章 苏诗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五十七章 吕公著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五十八章 善谏
- [ 免费 ] 第九百五十九章 进取之时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六十章 改制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六十一章 牡丹诗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六十二章 反咬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六十三章 朱婕妤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六十四章 老苏获释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六十五章 窦四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六十六章 招悔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六十七章 王珪的推荐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六十八章 窦仕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六十九章 皇帝看大象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七十章 御史清流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七十一章 廷对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七十二章 通通不认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七十三章 旧事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七十四章 禽兽不如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七十五章 老江湖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七十六章 始皇帝的问题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七十七章 思想问题才是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七十八章 军事
- [ 免费 ] 第九百七十九章 后勤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八十章 大宋该打的仗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八十一章 宜秋门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八十二章 一家子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八十三章 赵孝奕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八十四章 精微操作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八十五章 普遍公平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八十六章 证物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八十七章 补全证据链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八十八章 尉氏的变化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八十九章 扁罐
- [ 免费 ] 第九百九十章 汤泉
- [ 免费 ] 第九百九十一章 老父亲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九十二章 当家长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九十三章 论教育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九十四章 乒乓球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九十五章 保和春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九十六章 种山药的道理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九十七章 摸螺蛳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九十八章 鱼惊石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百九十九章 小苏文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章 冬蔬菜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章 有志者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章 热闹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章 膨化食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章 扑克牌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章 岛礁和泡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章 刨笔刀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章 君子小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章 经济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章 琥珀和珊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十章 苏油的不靠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十一章 太皇太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十二章 对皇帝的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十三章 逝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十四章 苏轼获释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十五章 工艺和技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十六章 受连累的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十七章 探讨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十八章 梦中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一十九章 以写入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十章 标准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十一章 郓州方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十二章 观量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十三章 坑辽人是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十四章 风气和国格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十五章 黄金不久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十六章 礼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十七章 曾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十八章 丑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二十九章 臣才天授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十章 基本教育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十一章 捧杀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十二章 很大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十三章 北苑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十四章 娟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十五章 下一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十六章 韩琦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十七章 大苏酿酒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十八章 问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三十九章 农业改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十章 字说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十一章 甲骨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十二章 徒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十三章 回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十四章 盛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十五章 苏鱼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十六章 说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十七章 发展路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十八章 饶骨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四十九章 大地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十章 圣旨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十一章 挨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十二章 石府的变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十三章 栓动小猎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十四章 蔡确的思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十五章 军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十六章 兴洛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十七章 蔡确的帮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十八章 学问还没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五十九章 骗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十章 就是骗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十一章 敲打清醒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十二章 讲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十三章 积极防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十四章 比烂的世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十五章 论党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十六章 大战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十七章 游牧与农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十八章 后勤到税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六十九章 和太后谈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十章 高滔滔哭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十一章 漕运改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十二章 蔡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十三章 使节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十四章 帮助辽国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十五章 体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十六章 音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十七章 定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十八章 大苏的传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七十九章 驮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十章 针锋相对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十一章 衡山之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十二章 毒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十三章 女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十四章 朝堂清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十五章 无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十六章 前三排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十七章 访谈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十八章 明润救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八十九章 上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十章 和蚨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十一章 金融业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十二章 惠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十三章 勾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十四章 戏精聚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十五章 日心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十六章 大变革前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十七章 运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十八章 死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零九十九章 动脑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章 大孩子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零一章 绝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零二章 廷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零三章 讨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零四章 谈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零五章 气跑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零六章 日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零七章 白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零八章 刺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零九章 妖师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一十章 矾楼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一十一章 年终总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一十二章 五泉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一十三章 室尚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一十四章 救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一十五章 上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一十六章 澶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一十七章 章大黑心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一十八章 十六时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一十九章 《瓠子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二十章 王克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章 老河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章 大河之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章 难熬的一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章 漕船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章 争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二十六章 守住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章 小侯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章 邢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章 惹不起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三十章 龟贼弄潮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章 漫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三十二章 改制第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章 好年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章 电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三十五章 獐子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章 故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章 傅贤妃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章 恐惧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章 见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四十章 共同利益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四十一章 城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章 西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四十三章 改制的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四十四章 名臣之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章 毕观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四十六章 药局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四十七章 爱读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章 穷人的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四十九章 谢罪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五十章 举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五十一章 知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五十二章 四代三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章 圣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章 阿司匹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章 敌友难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章 复行汉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章 谈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五十八章 敌人的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章 猜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六十章 聊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章 郑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章 欧阳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章 胡辣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六十四章 文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章 商都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六十六章 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章 故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章 检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章 密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七十章 教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七十一章 嵩阳兵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七十二章 田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章 狙击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章 再见沈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七十五章 货币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章 再见司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章 垄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章 卧云堂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章 论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八十章 高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章 县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八十二章 各有际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章 旧部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八十四章 赴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章 辛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八十六章 新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八十七章 文和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章 官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八十九章 七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九十章 反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章 化难为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九十二章 目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九十三章 立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九十四章 李清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章 忠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九十六章 破裂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章 种鄂的方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章 复盘汉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一百九十九章 我们该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零零章 准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零一章 车阵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零二章 准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零三章 司天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零四章 传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零五章 小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零六章 巧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零七章 文明之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零八章 新年将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零九章 打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一十章 学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一十一章 光禄寺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一十二章 玉料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章 入使线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一十四章 问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一十五章 占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一十六章 朝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一十七章 朝仪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一十八章 新气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一十九章 私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二十章 关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二十一章 形势不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二十二章 大移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二十三章 周全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二十四章 雄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二十五章 交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二十六章 金殿文元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二十七章 分歧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二十八章 进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二十九章 金明池聊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三十章 照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三十一章 战端再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章 小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三十三章 试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三十四章 凶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三十五章 献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三十六章 光屁股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三十七章 夜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三十八章 胜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三十九章 伐罪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四十章 自反而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四十一章 救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章 五台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四十三章 禅师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四十四章 帮助辽国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章 沈括所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章 又是交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四十七章 马蜂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四十八章 河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四十九章 老而弥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五十章 力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五十一章 王珪的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五十二章 欧阳夫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五十三章 苏油的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章 坟场游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五十五章 家庙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五十六章 经略六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五十七章 出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五十八章 顶级武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五十九章 两封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六十章 公然私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六十一章 正间反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六十二章 准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六十三章 动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六十四章 侦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六十五章 鏖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六十六章 狙击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六十七章 破阵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六十八章 民兵郭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六十九章 大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七十章 夜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七十一章 深夜报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七十二章 青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七十三章 矛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七十四章 演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七十五章 西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七十六章 开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七十七章 集体智慧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七十八章 延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七十九章 虚张声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八十章 小政委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八十一章 防辽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八十二章 闻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八十三章 招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八十四章 游说天都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八十五章 文钊投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八十六章 青冈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八十七章 动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八十八章 抵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 血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九十章 节奏乱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九十一章 背锅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九十二章 文武之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九十三章 战略调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九十四章 毕仲游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九十五章 大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九十六章 惨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九十七章 橐驼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九十八章 破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二百九十九章 大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零零章 评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零一章 矿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零二章 泡温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零三章 军事之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零四章 浑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零五章 我真的不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零六章 出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零七章 梁乙埋的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零八章 太后与皇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零九章 一手长刀,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一十章 接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一十一章 权力的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一十二章 聚歼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一十三章 种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一十四章 匪夷所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一十五章 种师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一十六章 推演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一十七章 操典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一十八章 悲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一十九章 临终对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二十章 意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二十一章 克灵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二十二章 收复河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二十三章 请罪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二十四章 作战计划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二十五章 内相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二十六章 美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二十七章 凉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二十八章 辽国变故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二十九章 对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三十章 祭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三十一章 回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三十二章 演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三十三章 风云再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三十四章 浮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三十五章 以子之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三十六章 无条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三十七章 疯狂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三十八章 文殊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三十九章 遗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四十章 驾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四十一章 仁多保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四十二章 劝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四十三章 新年前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四十四章 条陈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四十五章 得国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四十六章 崛起中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四十七章 老外的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四十八章 权力争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四十九章 西部大开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五十章 括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五十一章 抢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五十二章 快乐的赵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五十三章 骑兵合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五十四章 否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五十五章 凉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五十六章 优待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五十七章 居延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五十八章 肃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五十九章 河西学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六十章 敦煌遗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六十一章 刘猢狲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六十二章 潜在产能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六十三章 十六号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六十四章 磨合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六十五章 忽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六十六章 谁的首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六十七章 兰交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六十八章 国力的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六十九章 谈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七十章 丰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七十一章 软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七十二章 第一堂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七十三章 微言大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七十四章 金融操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七十五章 沈括入门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七十六章 贺兰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七十七章 名医之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七十八章 年报广告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七十九章 两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八十章 瑞升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八十一章 请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八十二章 思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八十三章 君臣对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八十四章 拍桌子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八十五章 铁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八十六章 兵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八十七章 白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八十八章 选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八十九章 安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九十章 富弼逝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九十一章 蒸汽机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九十二章 不信就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九十三章 无双国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九十四章 填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九十五章 大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九十六章 出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九十七章 金刚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九十八章 佛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三百九十九章 集体告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零零章 决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零一章 谋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零二章 鬼章的谋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零三章 学员斥候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零四章 阻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零五章 出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零六章 偷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零七章 东西皆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零八章 大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零九章 家国天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一十章 算计明白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一十一章 史书的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一十二章 新义之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一十三章 家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一十四章 急惊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一十五章 救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一十六章 电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一十七章 失踪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一十八章 旧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一十九章 招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二十章 反应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二十一章 守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二十二章 精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二十三章 计划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二十四章 四峰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二十五章 新眉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二十六章 《伦理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二十七章 交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二十八章 步兵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二十九章 大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三十章 战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三十一章 原始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三十二章 蔡京来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三十三章 探讨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三十四章 省费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三十五章 归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三十六章 消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三十七章 功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三十八章 暴发户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三十九章 证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四十章 木兰陂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四十一章 功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四十二章 理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四十三章 苏颂看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四十四章 扎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四十五章 风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四十六章 毒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四十七章 兄弟游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四十八章 步枪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四十九章 转轮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五十章 小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五十一章 一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五十二章 人性的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五十三章 风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五十四章 旅游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五十五章 文与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五十六章 主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五十七章 用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五十八章 培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五十九章 父子对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六十章 教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六十一章 陛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六十二章 建言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六十三章 大学堂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六十四章 弹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六十五章 教育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六十六章 纯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六十七章 府兵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六十八章 烧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六十九章 分割财产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七十章 纲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七十一章 挽救章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七十二章 摆事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七十三章 讲道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七十四章 神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 定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七十六章 总得讲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七十七章 授权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七十八章 忽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七十九章 弊病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八十章 议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八十一章 累不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八十二章 矛盾转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八十三章 外交乌龙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八十四章 来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八十五章 心理疏导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八十六章 辽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八十七章 发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八十八章 产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八十九章 农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九十章 园林设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九十一章 发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九十二章 旱情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九十三章 大爆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九十四章 火锅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九十五章 政治正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九十六章 抗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九十七章 光胫转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九十八章 新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四百九十九章 循循善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零章 问卷调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一章 潜移默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二章 大学堂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三章 饱便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四章 咆哮御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五章 矛盾根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六章 利弊之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七章 蔡确的下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八章 作相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九章 后世之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零九章 程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一十章 不善加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一十一章 好之乐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一十二章 科举改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一十三章 实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一十四章 水培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一十五章 盖棺论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一十六章 种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一十七章 算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一十八章 路途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一十九章 连机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二十章 打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二十一章 高手和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二十二章 辽国农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二十三章 到此为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二十四章 来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二十五章 阿骨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二十六章 完颜部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二十七章 经济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二十八章 经济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二十九章 司马光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三十章 锁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三十一章 金莲华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三十二章 宰相还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三十三章 通海之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三十四章 真道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三十五章 发展纲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三十六章 河北发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三十七章 弹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三十八章 御史的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三十九章 翰苑群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四十章 引领思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四十一章 苏辙上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四十二章 神宗归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四十三章 用不了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四十四章 统计数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四十五章 金殿捉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四十六章 忐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四十七章 贺礼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四十八章 特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四十九章 不速之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五十章 化肥和果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五十一章 一人一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五十二章 改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五十三章 贪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五十四章 韩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五十五章 得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五十六章 御屁股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五十七章 东胜祖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五十八章 神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五十九章 李格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六十章 丧心病狂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六十一章 颁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六十二章 华东心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六十三章 返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六十四章 杀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六十五章 想出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六十六章 天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六十七章 建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六十八章 黑心章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六十九章 冗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七十章 大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七十一章 耶律延禧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七十二章 攻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七十三章 范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七十四章 妖师叔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七十五章 头鱼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七十六章 苏半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七十七章 龙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七十八章 又见谤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七十九章终极解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八十章 共做习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八十一章 昭文相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八十二章 防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八十三章 新转般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八十四章 三君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八十五章 折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八十六章 大名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八十七章 故人之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八十八章 伪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八十九章 折继祖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九十章 又见董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九十一章 听介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九十二章 雅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九十三章 再见辛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九十四章 吴家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九十五章 烧曲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九十六章 价值洼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九十七章 磁州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九十八章 宝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五百九十九章 面粉厂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章 代笔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零一章 做局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零二章 孟端仪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零三章 突兀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零四章 送温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零五章 训小辈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零六章 开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零七章 本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零八章 钱可通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零九章 宝钞显灵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一十章 新版宝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一十一章 王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一十二章 二太守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一十三章 彩票漏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一十四章 好女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一十五章 春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一十六章 田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一十七章 嫁人的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一十八章 饯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一十九章 试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二十章 狗日的章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二十一章 巡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二十二章 炮楼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二十三章 请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二十四章 众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二十五章战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二十六章 杂货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二十七章 河间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二十八章 真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二十九章 支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三十章 改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三十一章 吏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三十二章 未来宰相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三十三章 调防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三十四章 入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三十五章 动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三十六章 殿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三十七章 龙门阵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三十八章 徐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三十九章 海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四十章 爷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四十一章 父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四十二章 小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四十三章 海军战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四十四章 海鬼爪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四十五章 清净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四十六章 万事俱备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四十七章 拦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四十八章 宫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四十九章 尚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五十章 古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五十一章 指点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五十二章 太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五十三章 脊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五十四章 来钱的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五十五章 名利兼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五十六章 广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五十七章 蕃坊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五十八章 打鱼摸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五十九章 诗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六十章 平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六十一章 理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六十二章 季常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六十三章 黑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六十四章 廷议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六十五章 方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六十六章 大订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六十七章 信用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六十八章 不武之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六十九章 不一样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七十章 一步又一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七十一章 还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七十二章 西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七十三章 念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七十四章 高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七十五章 功罪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七十六章 决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七十七章 大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七十八章 低调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七十九章 阳关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八十章 婚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八十一章 我亦作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八十二章 积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八十三章 止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八十四章 绝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八十五章 礼物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八十六章 不行特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八十七章 麻鱼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八十八章 大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八十九章 小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九十章 接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九十一章 交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九十二章 继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九十三章 张方平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九十四章 大练兵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九十五章 淞江一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九十六章 铁壳船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九十七章 安答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九十八章 咽不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六百九十九章 反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章 种五的朋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零一章 德政连连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零二章 没想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零三章 朝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零四章 想他们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零五章 翁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零六章 望苏亭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零七章 人皆有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零八章 美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零九章 见面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一十章 琉璃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一十一章 新情况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一十二章 册府元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一十三章 起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一十四章 求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一十五章 又遭弹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一十六章 善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一十七章 万人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一十八章 自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一十九章 却上心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二十章 力胜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二十一章 许炫富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二十二章 遗香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二十三章 后生可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二十四章 都艰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二十五章 诞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二十六章 女中尧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二十七章 亲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二十八章 海潮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二十九章 相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三十章 大军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三十一章 师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三十二章 李夔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三十三章 苍狼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三十四章 大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三十五章 后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三十六章 巡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三十七章 体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三十八章 岂止于此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三十九章 不习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四十章 大调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四十一章 困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四十二章 游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四十三章 不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四十四章 复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四十五章 苏油的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四十六章 赵煦的聪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四十七章 照相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四十八章 十一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四十九章 非汝辈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五十章 刘奉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五十一章 复杂成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五十二章 不足为惧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五十三章 不战而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五十四章 花塔子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五十五章 情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五十六章 克己新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五十七章 举措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五十八章 谋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五十九章 台球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六十章 马经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六十一章 破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六十二章 两国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六十三章 好运气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六十四章 老都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六十五章 无此君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六十六章 嘴炮狂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六十七章 新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六十八章 知识产权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六十九章 朝争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七十章 大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七十一章 奸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七十二章 解祸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七十三章 献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七十四章 回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七十五章 尽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七十六章 谁是大爷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七十七章 不答应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七十八章 少给脸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七十九章 铁甲舰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八十章 苏轼送东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八十一章 验收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八十二章 金大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八十三章 攻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八十四章 扫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八十五章 为公辟路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八十六章 举措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八十七章 复杂性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八十八章 小两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八十九章 设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九十章 高永昌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九十一章 消耗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九十二章 王爵酬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九十三章 大战的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九十四章 白驼沟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九十五章 惨败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九十六章出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九十七章 生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九十八章 大乱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七百九十九章 危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零零章 大账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零一章 觐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零二章 良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零三章 马彬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零四章 投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零五章 张叔夜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零六章 中秋会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零七章 化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零八章 侄子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零九章 旧城改造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一十章 收复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一十一章 晋王少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一十二章 寿昌更化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一十三章 幽云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一十四章 王师儒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一十五章 延禧之死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一十六章 敢成大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一十七章 局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一十八章 职责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一十九章 械斗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二十章 沙子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二十一章 瑕疵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二十二章 调整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二十三章 耶律南仙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二十四章 和亲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二十五章 武清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二十六章 水师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二十七章 老银币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二十八章 共情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二十九章 不宜语及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三十章 继任者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三十一章 逼宫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三十二章 倒绷孩儿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三十三章 弹劾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三十四章 风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三十五章 攻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三十六章 潜归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三十七章 危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三十八章 巧法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三十九章 收关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四十章 坦荡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四十一章 亡辽 ...
- [ 免费 ] 第一千八百四十二章 穿越者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章里老周写到,夔州以上, ...
杏书首页 我的书架 A-AA+ 去发书评 收藏 书签 手机
繁
第一千八百四十二章 穿越者
2021-7-9 21:49
千年之后,五苏祠。
导游小姐姐们穿着古代仕女服装,相貌温婉,身材婀娜,谈吐得体。
专业知识非常丰富才是重点。
说是祠堂,其实是一个大型纪念性场所,中间是一个大广场,广场左侧是眉山苏氏学术研究会,右侧是一个大型博物馆,前方真正的祠堂部分反倒是很小,乃是原纱縠行苏宅的旧址。
旧址仍然保持着原先的风貌,不过门口有一座石头屏风。
一位衣着朴素,戴着黑边眼镜,背着双背帆布书包,相貌文秀的年轻人,正看着上边镌刻的那首《卜算子》。
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
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
聘请来讲解的导游小姐姐对眼前这年轻人印象很好:“你是学生?哪个学校的?”
年轻人说道:“我是电子科大的,才从东胜州大湖区回来,刚在那边做完一个野牛电子跟踪的志愿项目,回来离开学还有几天假期,就来眉山玩玩。”
“哦。”小姐姐点头:“我也是志愿者,川大历史系的。”
说完开始对年轻人介绍:“这是苏文公《麈尘录》里的一首词,据他记载,乃是京师大学堂一名毛姓图书管理员所作,为平生最爱。”
“后人觉得,这首词和苏文公的生平,契合异常,故而颂扬得很广。建广场的时候,就将它刻在了这里。”
“京师大学堂毛姓的图书管理员?”年轻人回忆了一下:“好像没什么印象。”
小姐姐在心底里偷偷翻了个白眼:“是的,后人对苏文公生平追索极深,可是都没有找到这位管理员,也是个谜团了。”
带领着年轻人绕过是屏风,前方就是祠堂正门,门上挂着一块大匾额,匾额上四个飞白大书——“辅神庇圣”。
小姐姐解说道:“这道匾,是德宗皇帝赵茂亲笔御题。”
“说起来这里也是一桩公案。苏文公去世后,德宗皇帝命群臣拟文公哀荣,可文公历仕仁、英、神、圣、德五朝,功高盖世。群臣以为当在王安石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之上,然功绩太多,议论也就不一。”
“最后还是德宗定议,认为文公最大的功绩,在辅佐神宗,扶保圣宗,奠定千秋万代之丕基。于是亲书了‘辅神庇圣’这四字碑额。”
年轻人点了点头:“嗯,德宗这手飞白,倒是颇肖其祖,还青出于蓝。”
小姐姐稍微有些惊讶:“你有见识啊,大家都知道十一王爷瘦金体精妙,但是神宗的书法却因后来那次显谟阁大火,没有传世的。”
“有史载说他‘善飞白’,德宗仰慕神宗,自幼习练,也颇得神髓。”
年轻人笑了:“这字写得比他祖父好多了。”
小姐姐揶揄地笑道:“难道你还见过神宗的字不成?”
“啊?”年轻人不禁愣了一下,赧笑道:“有宋一朝,书风自苏黄米蔡方得大行,其后宫中才多有名师。”
“比如端王就是从黄山谷追求书道,因此后人迈越前人,也不奇怪。”
小姐姐抿嘴笑:“虽然有些道理,不过艺术和科学不一样,积累的东西一文不当,突破创新才价值千金。”
“赵佶乃是宗室里的书画天才,就算他的后人,也没有能迈过他的。”
年轻人微微一笑,也不想和漂亮小姐姐抬杠:“说得也是。”
等到进入祠堂,却是一个小方院,周遭都是售卖书籍、字画、刺绣、瓷器、美酒、小吃的专柜。
小姐姐说道:“当年纱縠行苏宅便是这样的结构,迎门的小院是接待丝绸商人,看样品的地方。苏文公改造川中丝织、纸墨、印刷、瓷器、酒业,造福千年,眉山的特产,这里都有。”
推销得很艺术,年轻人看了一圈,只对书籍比较感兴趣,于是来到专柜之前。
这里是琳琅满目的各种图书,除了当代名家对苏家各位人物所作的《评传》、《生平考》、《著作年表》、《轶事汇编》等论文类作品外,还有后人以他们为艺术形象,所创作的纪传体文学作品,既有古代评话、传奇,也有今人的小说。
然而这些,只占了整个书店的一半,另一半,则是苏家人的原著,堪称汗牛充栋。
每次带着游客来到这里,看着他们吃惊的样子,身为眉山人的小姐姐就不禁骄傲。
“这里都是苏氏一门所作的文字,包括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机械、化学、物理、数学、哲学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诗词、散文、戏剧理论、音乐理论、绘画理论、小说、奏议、书信等多种。”
“我们博物馆多年来一直在努力,整理出版苏门诸子的原稿高清影印版,一直没有停止过,让大家能够在阅读文字的同时,还欣赏到他们当时的书法,修改笔迹,创作心态。直到现在,都还没有出全。”
“因为根据不完全统计,光五苏祠的主角,苏颂、苏洵、苏油、苏轼、苏辙五位,他们的著述就高达八千万字,其中仅苏文公就多达五千万。”
“那是《麈尘录》和《伦理》的加成。”年轻人微笑摇头,突然问道:“《厨经》有多少字?”
“啊?”小姐姐不禁愣了一下,很少有游客会关心这个:“我只知道《厨经》记录了菜品六千七百多道,各式调料近百种,酒类六十多种,字数还真是不清楚。”
不过小姐姐很敬业,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:“我查查看……”
“不用不用。”年轻人赶紧制止:“我们继续吧。”
小院中间竟然是个供烧香烛的铁架,年轻人一看不禁莫名其妙:“这是干什么用的?”
小姐姐很无奈:“仅到绍圣年间,眉山苏氏就已经‘一门十进士,父子两探花’。”
“大家都说这里是天下文气所钟,每年都有很多考试的学子来这里参拜。”
“有些迷信的父母,还要在屋外燃香烛,好几次差点引发火灾。”
“最后博物馆觉得,不如专门给这些人设置一个烧香烛的地方,总比他们四处乱来的好。”
“啊?”年轻人不禁啼笑皆非:“当年京师大学堂可是有拿鸡蛋砸明润雕像的传统,怎么到现在还拜上了?”
“是吗?”这故事可是连小姐姐都没有听说过:“我怎么都不知道?”
“元符九年京师大学堂数学院的期末考试,压轴题就是苏明润出的,原题是——请证明:到平面上两定点距离比相同,且比值不为一的动点,其轨迹是一个圆,并请求出该圆半径。”
“一句话,五张草稿纸,绝大部分考生都吃了零蛋,于是愤怒的学生们跑去苏文公的雕像前拿鸡蛋回请他,因为听说苏文公从夔州任上就留下了病根,最讨厌吃鸡蛋。”
“打那时候起啊,每逢期末考,学院就形成了这么个传统,这叫‘拜苏公,破零蛋’。”
小姐姐听得娇笑不止,还真拿起手机查了查:“诶?你说的这道题还真有……不过苏文公是不是讨厌吃鸡蛋……诶,也查到了!”
当下手机:“但你说的学生砸雕像的事情却不见记载,肯定是骗人!再说了,活人为什么会塑雕像?”
“皇家杰出贡献终身成就奖啊,有塑像的!”年轻人有口难辨:“这是真事儿,估计……后来苏文公地位愈加崇高,朝廷将这事儿给禁了吧。”
说完不禁叹气:“设若苏文公在天有灵,只怕他更喜欢学生们请他吃鸡蛋,而绝不愿意享受这样的香火。”
小姐姐笑道:“苏文公不高崖岸,提举京师大学堂期间和学生们斗法的段子,都给编成笑话集了,就算拿鸡蛋砸他雕像,那也是喜欢他的一种表现。”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年轻人点头:“到了七十多岁,每年开学还要拿着扫帚去校门前冒充扫地老头,偷听新生对学校的印象和意见,接着聊天骗人家给学校提建议,可也是只有他才做得出来。”
说完补充了一句:“不过学生们真的非常喜欢他。”
走过小院就是祠堂正厅,迎面是三尊蜡像,手持牙笏端坐,两个紫袍一个红袍,倒是栩栩如生,中间的是苏颂、左边的是苏洵、右边的苏油。
这不是按照官位和成就来的,而是按照兄弟年齿来的。
旁边侧位也分坐了四人,里间两个年纪较大紫袍官员的相对而坐,一胖一瘦,乃是苏轼和苏辙,外边两个年纪较轻的也相对而坐,一个锦袍,一个紫袍,正是武职的扁罐和文职的漏勺。
外围还有一圈人物,都是朱紫锦袍加身,则都是四人的子嗣了。
小姐姐介绍道:“这里供奉的人物其实远不止五苏,不过祠堂最早建立于睿宗年间,当时只供奉了苏颂、苏洵、苏油、苏轼、苏辙五位,虽然后来做了增加,但是大家还是习惯叫这里五苏祠。”
“苏氏一门,苏颂做到了参知政事;苏辙做到了右仆射;苏油做到了左仆射;后来做到宰相的还有苏迈,苏轭,做到参政有苏迨,苏迟。加上做到使相的苏轶,时人称之为‘一门七相’。”
年轻人笑道:“苏子瞻大而化之,杵儿后来做了驸马,不然的话,怎么都应该一门九相才对。”
小姐姐点头表示同意。
欣赏过蜡像之后,转入后进,却是一间独立的祭室,同样是一奉四配十二哲的格局。
小姐姐介绍道:“德宗之后,苏文公地位越来越高,先是进入文庙,列于孔圣之侧。到一百二十年后的襄宗年间,始尊为理昭王,从文庙独立了出来。”
“祭典与文宣王、武成王比。以张载、陈昭明、苏容、陈梧为四哲,以沈括、邵伯温、卫朴、贾宪、朱吉、刘益、石通、李擎、李诫、毕观、郏亶、蔡京为十二贤配享。”
“尤其值得注意的,是其中有两名女性。苏容和毕观,她们也为理学的奠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这也是除女娲外,华夏第一次有女性得配文宣、武成、理昭级别的国家祭仪。”
“苏山长和观儿,她们当得起。”年轻人表示完全赞成。
“还有一点,陈昭明、苏容、陈梧,这本是一家子,这也是非常特殊的地方。”
“昭德有劳曰昭,能劳谦。圣闻周达曰昭,圣圣通合。”年轻人微微点头:“倒是妥帖,不过蔡京担任过两任首相,怎么却掉到了尾巴上?”
小姐姐说道:“这里只论学术,不论官阶,蔡京是以在经济学上的创建入选的。”
“那为何没有赵宗佑?”
“呃……”小姐姐越来越觉得眼前这年轻人不简单,连谥法都能张口就来,元符九年明算科试题这么冷僻的知识都知道,恐怕就连博物馆里的博士生都没这水平。
而所谈的话题,所问的问题,也总是在关键点上,赶紧解释道:“赵宗佑按道理说也应该配享的,不过当时议者认为他是宗室,不当在理昭王之下,与苏颂、苏八公、张方平同理,因此不入配享。”
年轻人伸出中指顶了顶眼镜架,嘀咕道:“这可就真是亏大了……”
从大殿里绕出来,却是一处后院花园的格局,那棵黄荆树,还有那棵荔枝树,都还在。
这里也被布置成一个小展览馆,陈列着几苏的仕途、成就、著作、交游等科普性的展板。
同样的,这里也有一个书店。
花园后面还有一个水榭,从水榭出去,就是一个新建的小公园。
小公园的草坪上,有几尊大理石雕刻的仕女。
小姐姐说道:“当时的苏家,是女性最自由一个团体,很多苏家女性,也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。刚刚那个书店里售卖的,都是她们的诗词、哲学、伦理、义理、音乐、金石、考古、评论等专著。这里是她们的雕像。”
年轻人一个个地认过去,观书的程夫人、制版的苏八娘,描瓷的二十七娘,仗剑的石薇,手持量角器的苏小妹,著书的毕观,都是或站或坐。
只有一个女子,拿着酒杯,以肘支身,仰视天上的白云,若有所思,那就是易安了。
毕观的身侧还有两名女性,一个年长的在调琴,年幼的在吹箫。
调琴的是绿箬,年幼的却不认得,年轻人不禁问道:“吹箫的这位是谁?”
导游小姐姐都惊着了:“你知识如此丰富,不知道她?她就是苏逗的妻子,华仙公主啊。”
“哦是她啊……”年轻人这才明白过来:“我只见过她小时候……”
“对。”导游小姐姐说道:“华仙和杵儿七岁同窗,十八岁成亲,大家对她印象最深的,就是七岁入学时,初次见面三难苏逗的故事。”
“嗯。”年轻人说道:“事后孟皇后就给两人定了亲。”
小姐姐继续说道:“结成夫妻后,二人跨过大海,华仙公主襄赞夫君治理新宋洲,聪慧仁德,土人以为神灵,也是了不起的女性。”
看过雕像继续向前走,公园里还有一个碑林,却是几苏和他们的门生故旧知交的相关书法作品,以及历代文人评价几苏功绩的诗词文章。
年轻人在这里所耗的时间最多,一路欣赏着,一路给小姐姐讲解碑上的法帖、信件、诗词的来历,还有人物之间的关系,作者的履历,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发生的许多故事。
后人的他不知道,但是与几苏同朝同时代的那些人,可以说一清二楚。
导游和游客到此来了个颠倒,小姐姐却听了个兴致盎然,心中对年轻人不禁越来越佩服。
等到来到一块碑前,年轻人停了下来:“诶?明润……呃苏文公这诗我却是没见过。”
小姐姐讶异道:“怎么可能?这首诗可是苏文公最有名的一首呢!”
年轻人又细读了一遍碑文:
蟆颐山下此江深,雨野烟亭次第分。
屐笠迟归穿鹿寨,囊壶几罄越藜门。
停叶瑶弦诚自晦,弥风松酒不长温。
桃花远意容吾醉,叵耐春溪易误人。
“没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啊?”
小姐姐抿嘴一笑,自己终于有胜过这年轻人的地方了:“苏文公晚年九十以后,据说人已经糊涂了,经常胡乱瞎画些素描,当时没人能够明白,文公画的到底是什么。”
“后来人们才发现,里边有大分子结构、脱氧核糖核酸、大型水电站、大客机、计算机、基站、火箭、卫星、空间站、潜艇……”
“再后来,一个叫二子的网络写手,从这些图画里得到了灵感,开了本连载,就是以苏文公为主角。”
“书中的文公,却是从我们现代穿越到古代去的。”
年轻人摇了摇头:“怎么可能?明润虽然学识丰赡,但那都是来自三坟五典,圣人经义,俯仰天地,综析人伦。”
“其诗词、文章、道德、义理……有岂是普普通通一个今人,穿越过去就能够轻松成就的?”
小姐姐笑道:“你这是专业人士的口吻,老百姓才不管呢,他们就喜欢猎奇。”
说完一指碑文:“而且人家还找到了证据。”
“证据?就这个?”
“你将这诗每句第五字连起来读一读。”
“此,次,穿,越,诚,不,容,易……啊哈?”
小姐姐得意地道:“这首诗也是苏文公作于九十之后。据说他那时最喜欢的,就是在艮岳下的芙蓉池钓鱼。”
“开始糊涂后,就常常把万岁山当成蟆颐山,把景龙江当做玻璃江,以为自己在眉山老家。”
“这就是苏文公最著名的‘穿越诗’,二子咬死说这就是证据,苏文公是今人穿越到古代的证据!”
“至于他的学识,那也是他穿到那边去后重新学的,这叫‘六经注我’!”
“现学的……”年轻人不禁恍惚了起来:“原来如此啊……”
“喂!”小姐姐伸手在年轻人眼前晃了晃:“你没事儿吧?”
看着小姐姐漂亮的小手,年轻人啼笑皆非地嘀咕道:“别说,还真有可能啊……”
“怎么可能?!”苏油很明显是小姐姐的偶像,急了:“那是二子混账!为了订阅故意歪曲我们华夏先人的成就,说得就跟我们捡现成便宜似的!”
“这么一说还是你有理。”年轻人立刻站到了小姐姐的这一边:“不是亲历者,都不知道那段时间的艰难……”
从五苏祠出来,小姐姐对年轻人的好感更是倍增,见年轻人同她告别,转身离开,咬咬嘴唇,突然喊道:“喂!”
年轻人转身:“还有事吗?”
小姐姐想了想:“你的历史知识真是渊博,我的导师陈鲁平先生正在招收宋代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,想不想试试?”
说完低了头:“这样你就是我师弟了……毕业后,还能一起留在博物馆工作……”
年轻人说道:“我是学信息工程的,历史只是爱好……”
小姐姐就好想吐槽,就你在碑林里说的那一通,你都是爱好,叫我这专业的情何以堪?
想了想,嗯,还是要给导师争取一下好苗子:“你熟悉《宋史》吗?”
年轻人说道:“熟悉倒是熟悉,不过我就只熟悉圣宗朝以上。”
“够了够了!仁英神圣,乃华夏数千年来最大变局!此次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就是这个。”
“除了个人传记和人物关系,你还有什么拿手的?历史方面?”
“个人传记和人物关系我只能叫一般,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朝政……”
小姐姐已经想捋袖子,再谦虚我可要打人了,却听年轻人继续说道:“拿手的嘛……主要还是古代数理,易数也还过得去,剩下的……大约就是十五志里的那部分——天文、五行、律历、地理、河渠、礼、乐、仪卫、舆服、选举、职官、食货、兵、刑、艺文。”
小姐姐都要哭了:“你到底是什么怪物?爱好者怎么可能喜欢那些?导师出题最喜欢从这些里边选,弄得人一个头两个大……”
说完摸出手机:“加微信加微信,以后你就是我的作业帮了。”
等两个人加了微信,年轻人问道:“你真觉得我行?”
“当然行!”小姐姐对年轻人比对自己还有信心:“十五志都能搞明白,导师以后绝对对你偏心……诶?你头像是个啥签名?干一?”
年轻人笑道:“这不是签名,这叫花押,代替签名用的。”
“这个也不是干一,却是三个数字的合体……二十一。”
《全书完》
完本感言
《苏厨》终于完本了。
从2018年11月16日开始,写到了2021年6月20日,前后花了两年半的时间。
这本书是老周的第二本长篇,和《山沟》一样,也是执念。
因此对成绩并不期待,开书之前也做好了心理准备,不如何失望。
老周有两个儿子,无论《山沟》,还是《苏厨》,其实都是想要留给他们的,一些精神方面的“储蓄”。
当然《苏厨》所想要讲的东西,比《山沟》多出了许多,结构也宏大了一些。
但是老周自己都想不到,篇幅会从原计划的三百万字,扩大到了四百八十万字,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计划,几乎从一本变成了两本。
老周的最初的大纲里里,故事的结尾,苏油放任赵煦死去,然后扶赵佶上台,他和蔡京两人轮流治政,彻底把控住朝堂,也从此彻底把控住历史的走向。
但是写到后来,老周无法如此下笔,因为老周发现苏油的性格,绝对不会像大纲里那样绝情,放任赵煦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死去。
这本书主角跨度时间很长,因而在写作的过程中,告别了很多值得尊敬的、让人喜爱的、笔锋一拐就可以改变命运的角色。
但是老周没法改,因为历史题材远比老周想象的困难,比如程夫人的命运,如果改掉,那么二苏的仕途轨迹也会跟着改变,两位角色的经历、著作,大苏那些美妙的诗词,就不可能存在了。
其它很多角色也有相似的问题,书里的《石钟山记》从苏轼的作品变成了苏逊的作品,就是例子。
类似的遗憾还有很多,老周也不忍心,但是因为能力不够,老周没法改变他们的命运,否则就会破坏全书的设定和架构。
开书之前,老周本来以为凭借自己的见闻阅历、多年思考,应该支撑得起这个题材。
然而事实证明老周过于自信了,写到后面越来越心虚,越来越觉得储备不够,很多书都需要重新读一读。
就跟书里曾经说过的那样,宋朝是一个被很多人误解很深的朝代,主要就是因为军事上的弱鸡,招致了过多鄙视的目光。
而秦朝、汉朝、唐朝、明朝,得到的待遇就好得多,很大的原因,其实就是对外战争胜利的加成。
很简单的两个例子,就能说明普通人对这个朝代的偏见。
一个就是很多人以为是真理的谬论——有宋一朝三百多年,起义四百多次。
老周已经在书里详细解释过这个误会的来龙去脉。
还有一次和作者——历史频道的作者——聊天的时候,那作者认为宋朝皇帝并不仁慈,给我截了一连串的截图,内容是宋神宗期间免除各地许多土贡,荔枝有多少颗,茶叶有多少饼。
那个数量看上去不少,比如荔枝,一万多颗。
那名作者的言下之意,是说宋代的君主是腐朽的统治阶级,他们所谓的“仁”是虚假的,他们为了享乐,施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负担,是沉重的。
他们免除这些土贡之旨意,就是他们之前压榨和剥削百姓的明证。
于是老周就问了他一句,其他朝代呢?
比如你崇尚的大明,你看的那篇文章,做过横向比较吗?
老周让他去查一查,看看历朝历代各地给中央的土贡数目有多少,然后再做一个横向的列表,之后,大家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
顺便给他也截了一个数字,明代初期,各地土贡数量高达两百多万斤,到明代中期,一度增加到近三百万斤。
当然之后就好多了,因为统治者嫌麻烦,直接改收银子了。即便这样,清代各地贡茶,也是以万斤为单位。
虽然他们还爱喝奶。
老周承认,所有封建王朝的君主,的确都是统治阶级代表,他们施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负担,的确也是沉重的,这一点,完全不存在什么问题。
但是罪孽有轻有重,至少北宋王朝的统治阶级,在某些方面作孽的程度,远比其他王朝的其他君主,要轻得多。
比如内官这个封建王朝最大的罪恶,宋神宗亲自裁定上限为一百人。
所以用那个资料来证明北宋王朝的万恶,是行不通的,得另找。
当然这些也不能说北宋的皇帝就有多好多自觉,很多时候,还和国力有关。
总之任何历史问题,都不要简单化的去看。
现在有一个让人担忧的现象,就是大家在看历史时候,看到的其实不是历史,而是一大堆的偏见,一大堆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东西。
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,主要是怕自家孩子变成那种靠短视频增长学问的人,老周才决定写这样一本书,想要传递一种信息。
历史其实也是一门科学,而且其实是最容易发现真相的科学。
历史有个好处,就是原始资料都在那里摆着,只要你愿意去寻找,总可以找到。
当然首先得有个怀疑的态度,才能产生疑问,之后才会去查实,不会不加选择地接受网上的那些转载再转载。
当然,还要记得查全面一些。
另一个大问题,就是史观。
无法保持一种平和冷静的,不偏不倚的,旁观者的姿态,是读不好历史的。
人类历史的进程,就是人类创造文明成果的进程,在这个进程中,经历了无数的摧毁和重建,而且负责摧毁和负责重建的,往往还是同一个团体,这些都得辩证地去看。
除了正常的三观以外,还有一条也容易被忽略,就是读史的时候,应该要怀着“人性”。
不要只看到表面文字上那些帝王将相们的丰功伟绩,也要多着眼于当时的百姓,看见那些丰功伟绩下他们付出的“牺牲”。
没有必要崇拜,如果用搞科研比喻读历史的话,那些历史人物,其实都应该是科研对象。
科学家会去崇拜小白鼠?最多止步于“喜欢”的程度就可以了。
中国的历史,因为“三讳”这个操蛋的传统,掩盖了太多的真相,塑造了太多的“完人”,读的时候尤其要小心。
一个被否定几千年的人,突然变成一个被大加颂扬的人;或者一个被颂扬几千年的人,突然变成一个被彻底否定的人,这种历史大风潮的转换,是否真实,是否合理,也要小心的评判。
可以选择随波逐流,因为必须要保护好自己,必须这样做,这个没问题。
但是随波逐流的时候,脑子也要清醒,心里也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,更要有一条底线。
说回本书,老周只能说,其中的历史人物的言谈,举止,互动,性格,老周都基本根据历史记载,有所加工,但尽量真实还原。
基本都有出处,不是胡乱编造。
比如苏油那年科举,就是当年的原题;比如吕公著的座右铭,他的那块砚台;比如黄庭坚的化石镇纸,都是有记录,甚至有实物的。
一些网上稀奇古怪的言论,比如范仲淹为何要写《岳阳楼记》袒护所谓的“贪官”?比如弹劾过欧阳修的蒋之奇,是否该用“奸臣”来定义?书中写到他们的时候,也顺便给了较为详细的解读,让大家看到当时事件和人物的复杂性。
对于两个重要人物——司马光和王安石,当很多人开始怀疑老周将他们的形象塑造得前后不一的时候,老周就知道了偏见的可怕。
原因就在于大家心目中,对这两个人物形象早有了预设,而且预设得非常单一。
比如司马光让出四个寨子给西夏,就在网上背上卖国贼的名声,宋神宗和王安石让地几百里给辽国,却依旧形象高大,原因就在于大家心里预设的坎,太高,太顽固,太难打破。
佛家有一个名词,专门解释这种现象——“知见障”。
导游小姐姐们穿着古代仕女服装,相貌温婉,身材婀娜,谈吐得体。
专业知识非常丰富才是重点。
说是祠堂,其实是一个大型纪念性场所,中间是一个大广场,广场左侧是眉山苏氏学术研究会,右侧是一个大型博物馆,前方真正的祠堂部分反倒是很小,乃是原纱縠行苏宅的旧址。
旧址仍然保持着原先的风貌,不过门口有一座石头屏风。
一位衣着朴素,戴着黑边眼镜,背着双背帆布书包,相貌文秀的年轻人,正看着上边镌刻的那首《卜算子》。
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
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
聘请来讲解的导游小姐姐对眼前这年轻人印象很好:“你是学生?哪个学校的?”
年轻人说道:“我是电子科大的,才从东胜州大湖区回来,刚在那边做完一个野牛电子跟踪的志愿项目,回来离开学还有几天假期,就来眉山玩玩。”
“哦。”小姐姐点头:“我也是志愿者,川大历史系的。”
说完开始对年轻人介绍:“这是苏文公《麈尘录》里的一首词,据他记载,乃是京师大学堂一名毛姓图书管理员所作,为平生最爱。”
“后人觉得,这首词和苏文公的生平,契合异常,故而颂扬得很广。建广场的时候,就将它刻在了这里。”
“京师大学堂毛姓的图书管理员?”年轻人回忆了一下:“好像没什么印象。”
小姐姐在心底里偷偷翻了个白眼:“是的,后人对苏文公生平追索极深,可是都没有找到这位管理员,也是个谜团了。”
带领着年轻人绕过是屏风,前方就是祠堂正门,门上挂着一块大匾额,匾额上四个飞白大书——“辅神庇圣”。
小姐姐解说道:“这道匾,是德宗皇帝赵茂亲笔御题。”
“说起来这里也是一桩公案。苏文公去世后,德宗皇帝命群臣拟文公哀荣,可文公历仕仁、英、神、圣、德五朝,功高盖世。群臣以为当在王安石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之上,然功绩太多,议论也就不一。”
“最后还是德宗定议,认为文公最大的功绩,在辅佐神宗,扶保圣宗,奠定千秋万代之丕基。于是亲书了‘辅神庇圣’这四字碑额。”
年轻人点了点头:“嗯,德宗这手飞白,倒是颇肖其祖,还青出于蓝。”
小姐姐稍微有些惊讶:“你有见识啊,大家都知道十一王爷瘦金体精妙,但是神宗的书法却因后来那次显谟阁大火,没有传世的。”
“有史载说他‘善飞白’,德宗仰慕神宗,自幼习练,也颇得神髓。”
年轻人笑了:“这字写得比他祖父好多了。”
小姐姐揶揄地笑道:“难道你还见过神宗的字不成?”
“啊?”年轻人不禁愣了一下,赧笑道:“有宋一朝,书风自苏黄米蔡方得大行,其后宫中才多有名师。”
“比如端王就是从黄山谷追求书道,因此后人迈越前人,也不奇怪。”
小姐姐抿嘴笑:“虽然有些道理,不过艺术和科学不一样,积累的东西一文不当,突破创新才价值千金。”
“赵佶乃是宗室里的书画天才,就算他的后人,也没有能迈过他的。”
年轻人微微一笑,也不想和漂亮小姐姐抬杠:“说得也是。”
等到进入祠堂,却是一个小方院,周遭都是售卖书籍、字画、刺绣、瓷器、美酒、小吃的专柜。
小姐姐说道:“当年纱縠行苏宅便是这样的结构,迎门的小院是接待丝绸商人,看样品的地方。苏文公改造川中丝织、纸墨、印刷、瓷器、酒业,造福千年,眉山的特产,这里都有。”
推销得很艺术,年轻人看了一圈,只对书籍比较感兴趣,于是来到专柜之前。
这里是琳琅满目的各种图书,除了当代名家对苏家各位人物所作的《评传》、《生平考》、《著作年表》、《轶事汇编》等论文类作品外,还有后人以他们为艺术形象,所创作的纪传体文学作品,既有古代评话、传奇,也有今人的小说。
然而这些,只占了整个书店的一半,另一半,则是苏家人的原著,堪称汗牛充栋。
每次带着游客来到这里,看着他们吃惊的样子,身为眉山人的小姐姐就不禁骄傲。
“这里都是苏氏一门所作的文字,包括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机械、化学、物理、数学、哲学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诗词、散文、戏剧理论、音乐理论、绘画理论、小说、奏议、书信等多种。”
“我们博物馆多年来一直在努力,整理出版苏门诸子的原稿高清影印版,一直没有停止过,让大家能够在阅读文字的同时,还欣赏到他们当时的书法,修改笔迹,创作心态。直到现在,都还没有出全。”
“因为根据不完全统计,光五苏祠的主角,苏颂、苏洵、苏油、苏轼、苏辙五位,他们的著述就高达八千万字,其中仅苏文公就多达五千万。”
“那是《麈尘录》和《伦理》的加成。”年轻人微笑摇头,突然问道:“《厨经》有多少字?”
“啊?”小姐姐不禁愣了一下,很少有游客会关心这个:“我只知道《厨经》记录了菜品六千七百多道,各式调料近百种,酒类六十多种,字数还真是不清楚。”
不过小姐姐很敬业,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:“我查查看……”
“不用不用。”年轻人赶紧制止:“我们继续吧。”
小院中间竟然是个供烧香烛的铁架,年轻人一看不禁莫名其妙:“这是干什么用的?”
小姐姐很无奈:“仅到绍圣年间,眉山苏氏就已经‘一门十进士,父子两探花’。”
“大家都说这里是天下文气所钟,每年都有很多考试的学子来这里参拜。”
“有些迷信的父母,还要在屋外燃香烛,好几次差点引发火灾。”
“最后博物馆觉得,不如专门给这些人设置一个烧香烛的地方,总比他们四处乱来的好。”
“啊?”年轻人不禁啼笑皆非:“当年京师大学堂可是有拿鸡蛋砸明润雕像的传统,怎么到现在还拜上了?”
“是吗?”这故事可是连小姐姐都没有听说过:“我怎么都不知道?”
“元符九年京师大学堂数学院的期末考试,压轴题就是苏明润出的,原题是——请证明:到平面上两定点距离比相同,且比值不为一的动点,其轨迹是一个圆,并请求出该圆半径。”
“一句话,五张草稿纸,绝大部分考生都吃了零蛋,于是愤怒的学生们跑去苏文公的雕像前拿鸡蛋回请他,因为听说苏文公从夔州任上就留下了病根,最讨厌吃鸡蛋。”
“打那时候起啊,每逢期末考,学院就形成了这么个传统,这叫‘拜苏公,破零蛋’。”
小姐姐听得娇笑不止,还真拿起手机查了查:“诶?你说的这道题还真有……不过苏文公是不是讨厌吃鸡蛋……诶,也查到了!”
当下手机:“但你说的学生砸雕像的事情却不见记载,肯定是骗人!再说了,活人为什么会塑雕像?”
“皇家杰出贡献终身成就奖啊,有塑像的!”年轻人有口难辨:“这是真事儿,估计……后来苏文公地位愈加崇高,朝廷将这事儿给禁了吧。”
说完不禁叹气:“设若苏文公在天有灵,只怕他更喜欢学生们请他吃鸡蛋,而绝不愿意享受这样的香火。”
小姐姐笑道:“苏文公不高崖岸,提举京师大学堂期间和学生们斗法的段子,都给编成笑话集了,就算拿鸡蛋砸他雕像,那也是喜欢他的一种表现。”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年轻人点头:“到了七十多岁,每年开学还要拿着扫帚去校门前冒充扫地老头,偷听新生对学校的印象和意见,接着聊天骗人家给学校提建议,可也是只有他才做得出来。”
说完补充了一句:“不过学生们真的非常喜欢他。”
走过小院就是祠堂正厅,迎面是三尊蜡像,手持牙笏端坐,两个紫袍一个红袍,倒是栩栩如生,中间的是苏颂、左边的是苏洵、右边的苏油。
这不是按照官位和成就来的,而是按照兄弟年齿来的。
旁边侧位也分坐了四人,里间两个年纪较大紫袍官员的相对而坐,一胖一瘦,乃是苏轼和苏辙,外边两个年纪较轻的也相对而坐,一个锦袍,一个紫袍,正是武职的扁罐和文职的漏勺。
外围还有一圈人物,都是朱紫锦袍加身,则都是四人的子嗣了。
小姐姐介绍道:“这里供奉的人物其实远不止五苏,不过祠堂最早建立于睿宗年间,当时只供奉了苏颂、苏洵、苏油、苏轼、苏辙五位,虽然后来做了增加,但是大家还是习惯叫这里五苏祠。”
“苏氏一门,苏颂做到了参知政事;苏辙做到了右仆射;苏油做到了左仆射;后来做到宰相的还有苏迈,苏轭,做到参政有苏迨,苏迟。加上做到使相的苏轶,时人称之为‘一门七相’。”
年轻人笑道:“苏子瞻大而化之,杵儿后来做了驸马,不然的话,怎么都应该一门九相才对。”
小姐姐点头表示同意。
欣赏过蜡像之后,转入后进,却是一间独立的祭室,同样是一奉四配十二哲的格局。
小姐姐介绍道:“德宗之后,苏文公地位越来越高,先是进入文庙,列于孔圣之侧。到一百二十年后的襄宗年间,始尊为理昭王,从文庙独立了出来。”
“祭典与文宣王、武成王比。以张载、陈昭明、苏容、陈梧为四哲,以沈括、邵伯温、卫朴、贾宪、朱吉、刘益、石通、李擎、李诫、毕观、郏亶、蔡京为十二贤配享。”
“尤其值得注意的,是其中有两名女性。苏容和毕观,她们也为理学的奠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这也是除女娲外,华夏第一次有女性得配文宣、武成、理昭级别的国家祭仪。”
“苏山长和观儿,她们当得起。”年轻人表示完全赞成。
“还有一点,陈昭明、苏容、陈梧,这本是一家子,这也是非常特殊的地方。”
“昭德有劳曰昭,能劳谦。圣闻周达曰昭,圣圣通合。”年轻人微微点头:“倒是妥帖,不过蔡京担任过两任首相,怎么却掉到了尾巴上?”
小姐姐说道:“这里只论学术,不论官阶,蔡京是以在经济学上的创建入选的。”
“那为何没有赵宗佑?”
“呃……”小姐姐越来越觉得眼前这年轻人不简单,连谥法都能张口就来,元符九年明算科试题这么冷僻的知识都知道,恐怕就连博物馆里的博士生都没这水平。
而所谈的话题,所问的问题,也总是在关键点上,赶紧解释道:“赵宗佑按道理说也应该配享的,不过当时议者认为他是宗室,不当在理昭王之下,与苏颂、苏八公、张方平同理,因此不入配享。”
年轻人伸出中指顶了顶眼镜架,嘀咕道:“这可就真是亏大了……”
从大殿里绕出来,却是一处后院花园的格局,那棵黄荆树,还有那棵荔枝树,都还在。
这里也被布置成一个小展览馆,陈列着几苏的仕途、成就、著作、交游等科普性的展板。
同样的,这里也有一个书店。
花园后面还有一个水榭,从水榭出去,就是一个新建的小公园。
小公园的草坪上,有几尊大理石雕刻的仕女。
小姐姐说道:“当时的苏家,是女性最自由一个团体,很多苏家女性,也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。刚刚那个书店里售卖的,都是她们的诗词、哲学、伦理、义理、音乐、金石、考古、评论等专著。这里是她们的雕像。”
年轻人一个个地认过去,观书的程夫人、制版的苏八娘,描瓷的二十七娘,仗剑的石薇,手持量角器的苏小妹,著书的毕观,都是或站或坐。
只有一个女子,拿着酒杯,以肘支身,仰视天上的白云,若有所思,那就是易安了。
毕观的身侧还有两名女性,一个年长的在调琴,年幼的在吹箫。
调琴的是绿箬,年幼的却不认得,年轻人不禁问道:“吹箫的这位是谁?”
导游小姐姐都惊着了:“你知识如此丰富,不知道她?她就是苏逗的妻子,华仙公主啊。”
“哦是她啊……”年轻人这才明白过来:“我只见过她小时候……”
“对。”导游小姐姐说道:“华仙和杵儿七岁同窗,十八岁成亲,大家对她印象最深的,就是七岁入学时,初次见面三难苏逗的故事。”
“嗯。”年轻人说道:“事后孟皇后就给两人定了亲。”
小姐姐继续说道:“结成夫妻后,二人跨过大海,华仙公主襄赞夫君治理新宋洲,聪慧仁德,土人以为神灵,也是了不起的女性。”
看过雕像继续向前走,公园里还有一个碑林,却是几苏和他们的门生故旧知交的相关书法作品,以及历代文人评价几苏功绩的诗词文章。
年轻人在这里所耗的时间最多,一路欣赏着,一路给小姐姐讲解碑上的法帖、信件、诗词的来历,还有人物之间的关系,作者的履历,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发生的许多故事。
后人的他不知道,但是与几苏同朝同时代的那些人,可以说一清二楚。
导游和游客到此来了个颠倒,小姐姐却听了个兴致盎然,心中对年轻人不禁越来越佩服。
等到来到一块碑前,年轻人停了下来:“诶?明润……呃苏文公这诗我却是没见过。”
小姐姐讶异道:“怎么可能?这首诗可是苏文公最有名的一首呢!”
年轻人又细读了一遍碑文:
蟆颐山下此江深,雨野烟亭次第分。
屐笠迟归穿鹿寨,囊壶几罄越藜门。
停叶瑶弦诚自晦,弥风松酒不长温。
桃花远意容吾醉,叵耐春溪易误人。
“没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啊?”
小姐姐抿嘴一笑,自己终于有胜过这年轻人的地方了:“苏文公晚年九十以后,据说人已经糊涂了,经常胡乱瞎画些素描,当时没人能够明白,文公画的到底是什么。”
“后来人们才发现,里边有大分子结构、脱氧核糖核酸、大型水电站、大客机、计算机、基站、火箭、卫星、空间站、潜艇……”
“再后来,一个叫二子的网络写手,从这些图画里得到了灵感,开了本连载,就是以苏文公为主角。”
“书中的文公,却是从我们现代穿越到古代去的。”
年轻人摇了摇头:“怎么可能?明润虽然学识丰赡,但那都是来自三坟五典,圣人经义,俯仰天地,综析人伦。”
“其诗词、文章、道德、义理……有岂是普普通通一个今人,穿越过去就能够轻松成就的?”
小姐姐笑道:“你这是专业人士的口吻,老百姓才不管呢,他们就喜欢猎奇。”
说完一指碑文:“而且人家还找到了证据。”
“证据?就这个?”
“你将这诗每句第五字连起来读一读。”
“此,次,穿,越,诚,不,容,易……啊哈?”
小姐姐得意地道:“这首诗也是苏文公作于九十之后。据说他那时最喜欢的,就是在艮岳下的芙蓉池钓鱼。”
“开始糊涂后,就常常把万岁山当成蟆颐山,把景龙江当做玻璃江,以为自己在眉山老家。”
“这就是苏文公最著名的‘穿越诗’,二子咬死说这就是证据,苏文公是今人穿越到古代的证据!”
“至于他的学识,那也是他穿到那边去后重新学的,这叫‘六经注我’!”
“现学的……”年轻人不禁恍惚了起来:“原来如此啊……”
“喂!”小姐姐伸手在年轻人眼前晃了晃:“你没事儿吧?”
看着小姐姐漂亮的小手,年轻人啼笑皆非地嘀咕道:“别说,还真有可能啊……”
“怎么可能?!”苏油很明显是小姐姐的偶像,急了:“那是二子混账!为了订阅故意歪曲我们华夏先人的成就,说得就跟我们捡现成便宜似的!”
“这么一说还是你有理。”年轻人立刻站到了小姐姐的这一边:“不是亲历者,都不知道那段时间的艰难……”
从五苏祠出来,小姐姐对年轻人的好感更是倍增,见年轻人同她告别,转身离开,咬咬嘴唇,突然喊道:“喂!”
年轻人转身:“还有事吗?”
小姐姐想了想:“你的历史知识真是渊博,我的导师陈鲁平先生正在招收宋代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,想不想试试?”
说完低了头:“这样你就是我师弟了……毕业后,还能一起留在博物馆工作……”
年轻人说道:“我是学信息工程的,历史只是爱好……”
小姐姐就好想吐槽,就你在碑林里说的那一通,你都是爱好,叫我这专业的情何以堪?
想了想,嗯,还是要给导师争取一下好苗子:“你熟悉《宋史》吗?”
年轻人说道:“熟悉倒是熟悉,不过我就只熟悉圣宗朝以上。”
“够了够了!仁英神圣,乃华夏数千年来最大变局!此次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就是这个。”
“除了个人传记和人物关系,你还有什么拿手的?历史方面?”
“个人传记和人物关系我只能叫一般,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朝政……”
小姐姐已经想捋袖子,再谦虚我可要打人了,却听年轻人继续说道:“拿手的嘛……主要还是古代数理,易数也还过得去,剩下的……大约就是十五志里的那部分——天文、五行、律历、地理、河渠、礼、乐、仪卫、舆服、选举、职官、食货、兵、刑、艺文。”
小姐姐都要哭了:“你到底是什么怪物?爱好者怎么可能喜欢那些?导师出题最喜欢从这些里边选,弄得人一个头两个大……”
说完摸出手机:“加微信加微信,以后你就是我的作业帮了。”
等两个人加了微信,年轻人问道:“你真觉得我行?”
“当然行!”小姐姐对年轻人比对自己还有信心:“十五志都能搞明白,导师以后绝对对你偏心……诶?你头像是个啥签名?干一?”
年轻人笑道:“这不是签名,这叫花押,代替签名用的。”
“这个也不是干一,却是三个数字的合体……二十一。”
《全书完》
完本感言
《苏厨》终于完本了。
从2018年11月16日开始,写到了2021年6月20日,前后花了两年半的时间。
这本书是老周的第二本长篇,和《山沟》一样,也是执念。
因此对成绩并不期待,开书之前也做好了心理准备,不如何失望。
老周有两个儿子,无论《山沟》,还是《苏厨》,其实都是想要留给他们的,一些精神方面的“储蓄”。
当然《苏厨》所想要讲的东西,比《山沟》多出了许多,结构也宏大了一些。
但是老周自己都想不到,篇幅会从原计划的三百万字,扩大到了四百八十万字,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计划,几乎从一本变成了两本。
老周的最初的大纲里里,故事的结尾,苏油放任赵煦死去,然后扶赵佶上台,他和蔡京两人轮流治政,彻底把控住朝堂,也从此彻底把控住历史的走向。
但是写到后来,老周无法如此下笔,因为老周发现苏油的性格,绝对不会像大纲里那样绝情,放任赵煦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死去。
这本书主角跨度时间很长,因而在写作的过程中,告别了很多值得尊敬的、让人喜爱的、笔锋一拐就可以改变命运的角色。
但是老周没法改,因为历史题材远比老周想象的困难,比如程夫人的命运,如果改掉,那么二苏的仕途轨迹也会跟着改变,两位角色的经历、著作,大苏那些美妙的诗词,就不可能存在了。
其它很多角色也有相似的问题,书里的《石钟山记》从苏轼的作品变成了苏逊的作品,就是例子。
类似的遗憾还有很多,老周也不忍心,但是因为能力不够,老周没法改变他们的命运,否则就会破坏全书的设定和架构。
开书之前,老周本来以为凭借自己的见闻阅历、多年思考,应该支撑得起这个题材。
然而事实证明老周过于自信了,写到后面越来越心虚,越来越觉得储备不够,很多书都需要重新读一读。
就跟书里曾经说过的那样,宋朝是一个被很多人误解很深的朝代,主要就是因为军事上的弱鸡,招致了过多鄙视的目光。
而秦朝、汉朝、唐朝、明朝,得到的待遇就好得多,很大的原因,其实就是对外战争胜利的加成。
很简单的两个例子,就能说明普通人对这个朝代的偏见。
一个就是很多人以为是真理的谬论——有宋一朝三百多年,起义四百多次。
老周已经在书里详细解释过这个误会的来龙去脉。
还有一次和作者——历史频道的作者——聊天的时候,那作者认为宋朝皇帝并不仁慈,给我截了一连串的截图,内容是宋神宗期间免除各地许多土贡,荔枝有多少颗,茶叶有多少饼。
那个数量看上去不少,比如荔枝,一万多颗。
那名作者的言下之意,是说宋代的君主是腐朽的统治阶级,他们所谓的“仁”是虚假的,他们为了享乐,施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负担,是沉重的。
他们免除这些土贡之旨意,就是他们之前压榨和剥削百姓的明证。
于是老周就问了他一句,其他朝代呢?
比如你崇尚的大明,你看的那篇文章,做过横向比较吗?
老周让他去查一查,看看历朝历代各地给中央的土贡数目有多少,然后再做一个横向的列表,之后,大家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
顺便给他也截了一个数字,明代初期,各地土贡数量高达两百多万斤,到明代中期,一度增加到近三百万斤。
当然之后就好多了,因为统治者嫌麻烦,直接改收银子了。即便这样,清代各地贡茶,也是以万斤为单位。
虽然他们还爱喝奶。
老周承认,所有封建王朝的君主,的确都是统治阶级代表,他们施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负担,的确也是沉重的,这一点,完全不存在什么问题。
但是罪孽有轻有重,至少北宋王朝的统治阶级,在某些方面作孽的程度,远比其他王朝的其他君主,要轻得多。
比如内官这个封建王朝最大的罪恶,宋神宗亲自裁定上限为一百人。
所以用那个资料来证明北宋王朝的万恶,是行不通的,得另找。
当然这些也不能说北宋的皇帝就有多好多自觉,很多时候,还和国力有关。
总之任何历史问题,都不要简单化的去看。
现在有一个让人担忧的现象,就是大家在看历史时候,看到的其实不是历史,而是一大堆的偏见,一大堆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东西。
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,主要是怕自家孩子变成那种靠短视频增长学问的人,老周才决定写这样一本书,想要传递一种信息。
历史其实也是一门科学,而且其实是最容易发现真相的科学。
历史有个好处,就是原始资料都在那里摆着,只要你愿意去寻找,总可以找到。
当然首先得有个怀疑的态度,才能产生疑问,之后才会去查实,不会不加选择地接受网上的那些转载再转载。
当然,还要记得查全面一些。
另一个大问题,就是史观。
无法保持一种平和冷静的,不偏不倚的,旁观者的姿态,是读不好历史的。
人类历史的进程,就是人类创造文明成果的进程,在这个进程中,经历了无数的摧毁和重建,而且负责摧毁和负责重建的,往往还是同一个团体,这些都得辩证地去看。
除了正常的三观以外,还有一条也容易被忽略,就是读史的时候,应该要怀着“人性”。
不要只看到表面文字上那些帝王将相们的丰功伟绩,也要多着眼于当时的百姓,看见那些丰功伟绩下他们付出的“牺牲”。
没有必要崇拜,如果用搞科研比喻读历史的话,那些历史人物,其实都应该是科研对象。
科学家会去崇拜小白鼠?最多止步于“喜欢”的程度就可以了。
中国的历史,因为“三讳”这个操蛋的传统,掩盖了太多的真相,塑造了太多的“完人”,读的时候尤其要小心。
一个被否定几千年的人,突然变成一个被大加颂扬的人;或者一个被颂扬几千年的人,突然变成一个被彻底否定的人,这种历史大风潮的转换,是否真实,是否合理,也要小心的评判。
可以选择随波逐流,因为必须要保护好自己,必须这样做,这个没问题。
但是随波逐流的时候,脑子也要清醒,心里也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,更要有一条底线。
说回本书,老周只能说,其中的历史人物的言谈,举止,互动,性格,老周都基本根据历史记载,有所加工,但尽量真实还原。
基本都有出处,不是胡乱编造。
比如苏油那年科举,就是当年的原题;比如吕公著的座右铭,他的那块砚台;比如黄庭坚的化石镇纸,都是有记录,甚至有实物的。
一些网上稀奇古怪的言论,比如范仲淹为何要写《岳阳楼记》袒护所谓的“贪官”?比如弹劾过欧阳修的蒋之奇,是否该用“奸臣”来定义?书中写到他们的时候,也顺便给了较为详细的解读,让大家看到当时事件和人物的复杂性。
对于两个重要人物——司马光和王安石,当很多人开始怀疑老周将他们的形象塑造得前后不一的时候,老周就知道了偏见的可怕。
原因就在于大家心目中,对这两个人物形象早有了预设,而且预设得非常单一。
比如司马光让出四个寨子给西夏,就在网上背上卖国贼的名声,宋神宗和王安石让地几百里给辽国,却依旧形象高大,原因就在于大家心里预设的坎,太高,太顽固,太难打破。
佛家有一个名词,专门解释这种现象——“知见障”。